读书会在我国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开展互动阅读活动的学习社群,是三人及以上成员出于特定目的而自发形成的组织,因此,民间读书会占据多数。按形成方式分类,读书会可以分为自发性读书会和派生性读书会,后者通常会依托于某一机构,如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媒体运行的读书会,如“搜狐读书会”“腾讯思享会”“凤凰网读书会”等,书店和出版机构运行的读书会以及阅读类公号成立的读书会等,派生性读书会多是自身业务延伸而成立;按阅读内容分类,有人文社科类读书会、国学读书会、亲子教育读书会、经管读书会、精神共修读书会、科技读书会等;按活动开展方式,有研读会、精读类、享读会、讲读会等,有些强调领读者引领,有些则主张人人分享。按照运营模式划分,又可以将读书会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读书会,樊登读书会、燕乌集阙读书会、浩途家庭俱乐部等都实行会员收费制实现商业化转型,可以归为盈利性读书会,非盈利读书会则是由创始人出于兴趣将志同道合的读友聚合,受权力、资本的影响小,更强调读书的纯粹性。事实上,是否以公益为目的很难从根本上区分,很多能够盈利的读书会也会带来公益效果,许多公益活动的背后,也存在商业行为。
公益读书会:资源整合化解发展困境
资金、场地、管理者的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困扰读书会的三大难题。但是在今年的采访中,更多读书会负责人不再认为这些因素是头号难题,如何提高主题策划的合理性、提高参与者的参与热情和互动性取而代之成为读书会负责人重点思索的问题。这与经过几年的野蛮发展后,读书会逐渐明晰自身定位,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并形成有效的管理体制不无关系。
从目前来看,公益性读书会目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获得资金、场地等资源的支持:一是政府部门通过经费补贴、购买服务、政策照顾等提供帮助,二是企业捐赠,三是个人捐赠。嘤鸣读书会创始人赵健就谈到,尽管会限制自身独立性,但与政府合作不失为一种安全的资金渠道,政府采购服务、申请公益创投是嘤鸣读书会重要资金来源。“很多公益组织不和政府合作,大多是信息不对称、双方不信任等原因造成的。”后院读书会的活动开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早在2013年时就曾获得深圳读书月活动承办权。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就是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所属企事业单位而成立的。深圳读书会通过游说、吸纳多家高端行业的企业作为理事会成员而得到相对充裕的资源支持,还通过承办、联合开展、提供创意及服务等方式,与各区图书馆、小型书吧建立场地伙伴。
读书会应该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的问题,也不再是值得争议的话题。在相聚星期三创始人王肖杰看来,“一是想不想,二是能不能,想赚又能赚,何乐不为,想赚不能赚,就学,能赚不想赚,可以当作乐趣”。王肖杰表达了其对读书会是否该盈利的看法。
商业运作“蔚然成风”
相对来说,商业化运作的读书会更容易形成强大的自我发展机制,更为活跃。“知识付费”成为2016年的重要关键词。读书会当前最常采用的收费方式还是会员付费。樊登读书会成为商业运作的典型案例。据悉,到2016年10月,成立于2013年11月的樊登读书会,经过3年多的发展,已成立包括地市级在内的242家分会,并逐步开展与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会员只需付费365元,就可以获得每年50本精选图书的图文、音频和视频的服务机会,还可以参与线下书友分享会。据介绍,樊登读书会的会员定位在25~45岁的中产阶级,精读的书目聚焦事业、家庭、心理三方面,目标是“帮助那些没有时间读书、不知道读哪些书和读书效率低的人群每年吸收50本书的精华内容。”因为聚集大量特定人群,樊登读书会逐渐拓展与出版机构的合作,推出读书会员的专属版图书,并在尝试将线上的影响力转移到线下实体书店。樊登的个人影响力、精准的读者定位、合理的读书会选题策划等都是樊登读书会能够持续稳定运营的重要因素。风投的引入同时也保障了樊登读书会充足的资金流。
2016年,部分读书会通过线上的影响力取得了广告投放收入,甚至发起线上培训课程、开设微店,拓宽了线上的盈利方式。
不难看出,读书会已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阅读组织形式,不只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专业化的运作让读书会具备了更多延伸功能。如阅读邻居读书会发起了“DIAO包计划”,开创读者盲买的模式;人民出版社读书会既向读者推介好书,同时也在探索传统出版业营销模式转变的路径;亲子类读书会的商机更是显而易见,已经成为连接出版社、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纽带;媒体类读书会为媒体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等。消费的升级、全民阅读高潮的到来必将催生更多形式多样、有趣、有料的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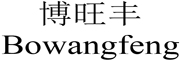








 纸友
纸友
 行情
行情
 订单
订单
 广告
广告
 找货
找货
 签到
签到

 关注
关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