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文章表示,与上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产能过剩完全不同,新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石油、煤炭、钢铁及水泥、玻璃等上游地带,也就是重化工行业,该行业不仅具有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的硬伤,而且更有生产连续性强的软肋,即整个生产线一旦点火生产就不能轻易停产。而目前重化工行业产品已全线绝对过剩,同时遭遇国内经济新常态叠加期,企图通过传统的稳增长和扩大需求方式来化解过剩产能已不现实,产能最终出清的难度可见一斑。
文章称,市场化无疑是处置过剩产能的最主要手段,不过,市场化主要是指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而市场化的开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比如通过政府提高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行业标准就可迅速而有效淘汰“僵尸企业”,通过政府设置产业亏损标准,就可加速关停并转与重组剥离,通过政府牵线搭桥,可拓展企业产能输出的渠道等等。市场与政府若能无缝契合与精确匹配,就能产生资源配置的化学反应。 但政府在去产能过程的作用也不应仅停留在政策训导、标准引领等间接推动层面。近几年,围绕着化解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症结,国务院出台了不少文件,但最终效果甚微,去产能如今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已然形成了一种怠惰与懒政的惯性力量;特别产能过剩的矛盾本身就由一些地方政府追求产业扩张与漠视结构趋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酿造,而为维护本地财政税源及减少失业压力,有些地方政府针对去产能会通过变通手段打“太极”;由于担心去产能会导致呆账变成坏账并引致不良资产的上升从而侵蚀利润,银行也不想去为化解产能主动作为;至于企业,一方面重化工行业的盈亏平衡点距离关门歇业点还有一段距离,而国企都缺乏硬预算约束,能活一天就争取多活一天的不在少数。如此看来,单凭市场力量并不能保证化解产能的效果如期落地,我国特定的商业环境需要行政力量尤其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甚至强权渗透。 文章认为,资产处置与人员安置是“去产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问题。前者可通过衰退产业退出援助计划逐步解决,后者可通过综合福利计划的实施来缓解。在资产处置上,中央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补助地方和企业筹集的化解过剩产能资金,还可考虑由地方政府发行长期专项债券,按相关省份减产规模对应确定债券发行额度,由省级政府发债并偿还,中央政府给予贴息补助;与此同时,提倡和允许银行牵头银团贷款(特别民营金融组织)参与企业并购重组,支持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转为银行对企业持股,另可通过既有或新设的资产管理公司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将不良资产打包管理,再通过之后有序的证券化逐步化解金融风险。在人员安置上,中央政府应从“去产能”的财政专项资金中划出固定比例予以定向安排;对承接再就业员工的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应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与政策倾斜;与此同时,配合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从债务重组中退出的国有资本充实到社保资金账户中来,稳定和适度增加失业人员的社保资金供给。 中央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所担纲的主要是顶层设计及足量政策驱动和必要的行政干预等职能,而真正落实还有赖于地方政府,为此,除了为地方政府制定明确的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与具体指标并加强全程监督与严格问责外,中央政府还应当建立针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如可考虑设置“过剩行业减产转型基金”,并由发债资金补充,而在基金使用上,可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和创新空间。还可以允许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开交易过剩产能,如经济强弱的两省各需要分别减产100万吨,可允许其中经济强省到弱省购买100万吨减产配额,同时不用化解自己的产能,而卖方拿到资金后可用于对关闭、退出企业的补助。 文章指出,表面上看,化解过剩产能在做减法,其实“去产能”饱含着丰富的增量含义。化解产能过剩离不开厚实的财力支持,为此需要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释放充沛的流动性,更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码用力;由于“去产能”中会发生高频快捷的重组并购,就需要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与活跃;因为部分过剩产能并非因为周期性而是由于未能与市场需求对接而产生,这又需要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的步伐。另外,如果说“去产能”是阶段性任务,则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再造经济成长新动能则是长久性话题,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完备而灵活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创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保护制度。 文章最后说,不仅“去产能”过程要严控新增产能,产能出清后更应建立长效协防机制。为此,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设定相关行业的总量“天花板”,并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常态监督与及时纠错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进一步张扬市场优胜劣汰的自我整合与净化功能。作为今年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首要任务,去产能近期被国家领导人反覆提出,这预示着基于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多政策措施将很快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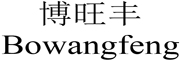








 纸友
纸友
 行情
行情
 订单
订单
 广告
广告
 找货
找货
 签到
签到

 关注
关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